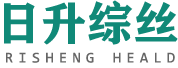锦绣与中华传统审美文化
■演讲人:古风 ■演讲地点:扬州大学文学院 ■演讲时间:二○一六年三月
古风 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延安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古代文论学会常务理事。主要是做中国文论和美学研究,发表论文150多篇,出版专著多部,代表作有《意境探微》和《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存活论》。论文入选了第18届(北京)和第19届(波兰)世界美学大会。
(了解更多光明讲坛内容请扫描二维码关注光明讲坛公众微信号。欢迎大家留言、探讨、推荐。)
丝绸是一项古老而伟大的发明,并从东到西、从陆地到海洋铺设出了色彩斑斓、富丽堂皇和波澜壮阔的丝绸之路,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所作出的重要贡献。2009年9月30日,“中国蚕桑丝织技艺”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从此中华丝绸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丝绸薄如蝉翼,轻似云霓,美若彩霞。自古以来,人们就将丝绸作为“美物”来看待。丝绸的种类较多,包括绢、缎、罗、纱、绡、纨、绨、缯、绮、绫、锦等,宛如百花盛开,各有其美。其中织锦的出现,将丝绸审美文化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是中华丝绸审美文化史上的奇葩。所谓锦,就是用彩色丝线织成花纹图案的丝绸。它色彩斑斓,图案华丽,是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高等丝绸。譬如新疆出土的汉代著名的《红地韩仁绣锦》就具备极其重大的审美价值。它是在红色地锦上,织绣着具有汉代特征的图案,即云气纹、动物纹和吉祥语的组合。云气纹,也称为祥云纹,是汉代丝绸锦绣的标志图案,后来成为中华传统审美文化的图像符号。动物纹从右至左依次为狮、辟邪、虎、羊、龙等,吉祥语从右至左依次为“韩仁绣文衣、右子孙无亟”10字穿插在花纹的空隙处。韩仁是西汉著名的织绣艺人。“右”与“佑”通用,“亟”与“极”通用,即永远保佑子孙。这件作品色彩丰富,图案华美,是汉代织锦的代表作。后来,织锦技艺,如花绽放,形成了蜀锦(成都)、宋锦(苏州)和云锦(南京)三大名锦。蜀锦图案华美,精湛高贵;宋锦花纹精致,色彩典雅;云锦色泽光丽,灿若云霓。各有特色,美不胜收。
所谓绣,又称为刺绣,民间也叫作“绣花”,是以穿针引线的方法,将某些花纹图案缝制在织物(布料、丝绸)上。从《诗经》文献来看,诸如“素衣朱绣”(《唐风·扬之水》)、“衮衣绣裳”(《豳风·九罭》)和“黻衣绣裳”(《秦风·终南》)等,周代在丝绸衣服上绣花已比较普遍了。这种“绣衣”的传统发展到宋代,有了革命性的转变,一是朝廷专门设立了“文绣院”,绣工巧手达到300多人,专为皇宫绣制御衣和装饰品;二是形成了以唐宋名家书画为范本的画绣。因为,宋代之前刺绣以实用为主,从宋代开始除了实用绣品之外,也有了艺术绣品。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海棠双鸟》、《梅竹鹦鹉》和《瑶台跨鹤》便是南宋画绣精品。后者以松枝、楼台、祥云、山石和松树构成一个半圆形画面,上方有一位仙人骑鹤翩翩而来,楼台上有二人说笑着迎接,形成构图上的照应关系,一方印章就嵌在下半圆的左尾。人物传神,构图精巧,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正如董其昌《筠清轩秘录》所说:“宋人之绣,……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设色精妙,光彩夺目。山水分远近之趣,楼阁得深邃之体,人物具瞻眺生动之情,花鸟极绰约噏唼之态,佳者较画更胜。”移用这段话评价《瑶台跨鹤》可谓恰当。这种“画绣”技艺通过明代顾绣传承于后世。清代以降,形成了苏绣、蜀绣、粤绣和湘绣四大名绣。苏绣平齐细密,素雅柔美;蜀绣针法多样,疏朗明快;粤绣构图饱满,色彩鲜艳;湘绣丝绒结合,形神兼备。绣花朵朵,各有其美。
虽然,从性质上看,“绣”不是丝绸,但在古代一般常用彩丝和丝绸作为刺绣的材料,因而“绣”与丝绸就有了密切的关系。由于所用材料相同(如彩丝),表现对象相同(如花纹图案),因而古人常常以“锦”与“绣”并称(锦、绣)或者合称(锦绣)。但是,“锦”与“绣”两者的工艺技术不同,前者是“织”成花纹图案,后者则是“绣”成花纹图案。所以,“锦”是锦,“绣”是绣,前者是丝绸,后者只是丝绸的装饰技艺和装饰品。但是,锦与绣有相同点,即两者工艺最复杂、色彩最丰富和图案最华丽,是最具有观赏性的丝绸。因此,锦绣是中华丝绸审美文化的精华。
色彩是人类视觉快感的第一种形式,因而色彩观念就是人类最初形成的审美观念。所以,要考察一个民族的审美观念起源,就应当从考察这个民族的色彩观念开始。那么,中华民族是如何从色彩的认识开始建立自己的审美观念呢?锦绣与中华原初色彩观念的形成又有啥关系呢?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我认为,人类原初色彩观念的形成,基本上经过了两个阶段:一是观看阶段。天上的日月星云,地上的山水草木,以及花鸟虫鱼等,都是有色彩的。可以说,凡是太阳下面的事物都富有色彩。所以,当人类出现在地球上时,面前便是一片色彩斑斓的世界。对这种的彩色世界,人类最初能做的事情就是观看→认识→再观看,即被动地接受这些色彩信息。二是创造阶段。人类在对于色彩认识的基础上,能发现、制造和利用颜料,并利用人造色彩美化生活用品。我们祖先创造的第一类染色生活用品是原始彩陶,可称为彩陶时代。原始彩陶的发明缘于食,是餐饮器皿的审美化。有的人觉得,原始彩陶只有赤、白、黑三种色彩。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原始彩陶的最大成就是基本确立了赤、白、黑、黄、青(蓝)五色观念。这与《尚书·益稷》对于“五色”的记载是相吻合的。虽然这一段时期我们祖先的色彩观念还比较单纯,即没有对于色彩赋予更多的人文内涵。我们祖先创造的第二类染色生活用品是锦绣,可称为锦绣时代。锦绣的发明缘于衣,是服饰用品的审美化。他们不但可以先织后染,创造印花丝绸;也可以先染后织,创造华丽锦绣。因此,锦绣的出现是丝绸生产技艺成熟的标志,也是中华色彩观念成熟的标志。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这一段时期,我们祖先已经能够认识、提炼和利用植物染料。诸如从茜草中提炼红色颜料,从荩草中提炼黄绿色颜料,从蓝草(马蓝草、木蓝草、槐蓝草)中提炼蓝色颜料,从紫草中提炼紫色颜料等。《诗经·小雅·采绿》就是抒写一位妇女采摘染料植物的诗歌。朱熹注云:“蓝,染草也”。植物染料的发现和利用是一大进步。其二,这一段时期,我们祖先已形成了利用人造颜料装饰和美化生活用品的审美意识。其三,这一段时期,我们祖先已形成了“五色”观念。《考工记》云:“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彩备谓之绣。”彩陶时代形成了“五色”观念,锦绣时代“五色”观念得到了继续巩固。东汉织锦常用红、蓝、黄、绿、白五种色彩,是五色观念的具体实践。譬如著名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就是在蓝地上,织绣了红、黄、绿、白花纹,合为五色,是典型的东汉织锦的代表作。这件织锦“总五色而极思,尽众化之为形”(张率《绣赋》),具备极高的审美价值。其四,随着染丝、染绸和印花技术的发展,这时人们已经掌握了以正色来配制间色的技术,大大丰富了色彩的种类。譬如在《说文解字》中收入不同色彩的丝织品就有35种之多。这是古代的文献证据。汉代墓葬出土的织锦有绛、白、黄、褐、宝蓝、淡蓝、油绿、绛紫、浅橙、浅驼等10多种色彩,其中大多是配制的间色。这是古代的实物证据。也有人对于吐鲁番出土的唐代丝绸作过色谱分析,共有24种颜色,其中大部分是间色。这是古代的科学证据。因此,我认为,丝绸锦绣的色彩是十分丰富的,此时人们已经掌握了间色配制技术,使色彩的种类增加到数十种之多。所以,在色彩观念上,锦绣时代比彩陶时代又前进了一大步。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人们是在丝绸锦绣生产中丰富了对于色彩的认识,所以也就将色彩与丝绸锦绣联系在一起了。尤其是在对于一些色彩的命名用字中,更能够正常的看到丝绸锦绣对于原初色彩观念的形成起了及其重要的作用。譬如“红”、“绿”、“紫”、“绛”、“缃”、“绯”、“缁”等表示色彩的文字皆与丝绸锦绣有关。如《说文》云:“红,帛赤白色”;“绿,帛青黄色也”;“紫,帛青赤色”;“绛,大赤也”;“缃,帛浅黄色也”;“绯,帛赤色也”;“缁,帛黑色也”等。虽然丝绸锦绣并不是提炼色彩的原料,但是人类对于色彩种类的发现和利用确实与丝绸锦绣的生产需求有关,所以就用各种色彩的丝绸锦绣作为标识色彩的文字。这是人们为何需要用丝绸锦绣的名称(文字)标识色彩的真实原因。因此,在这些标识色彩的文字里就永远积淀下了丝绸锦绣的痕迹。这足以证明,丝绸锦绣与中华原初色彩观念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
锦绣不仅美化了人们的生活,而且也促使人们形成了新的审美观念。由于色彩丰富,图案华丽,因而锦绣成为丝绸中最美丽的品种。所以,从商周至战国时期的人们观念中,“锦绣”是美丽之物,而且是一切美丽事物中的最美者,因而被称为“美物之首”。
早在商周时期,锦绣除了用来制作贵族的衣服之外,还用于居室装饰。据说商纣王生活十分奢侈,其宫殿“锦绣被堂”(墨子语)。这是说用锦绣制作窗帘、帐幔、墙围、壁挂等,使居室华美多彩,富丽堂皇。这种以锦绣美化生活的风气在战国时期更为流行。例如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共出土46件丝织品,计有衾、衣、袍、裙、绔、衿、帽、鞋、镜衣、枕套等,涉及到绢、纱、罗、绨、组、绦、绮、锦等丝绸品种,被称为“战国丝绸宝库”。当然,这种审美时尚还只是局限于贵族社会,宋元以后随着丝绸产业的发展,民间百姓也能够正常的使用丝绸锦绣了。大致说来,锦绣被作为审美元素,被广泛地使用于衣服、被面、枕套、鞋垫、腰带、披风、纱巾、手绢、纨扇、荷包、帐幔、壁挂、屏风、门帘、锦旗、幌子、书籍、字画等用品,美化了人们的生活。民间祥瑞文化的花纹图案,诸如龙凤、鸳鸯、喜鹊、仙鹤等飞禽,梅、兰、松、竹等花草,鹿、麒麟、马、虎等动物,都成为锦绣常用的题材。正如李卓明的《丝绸之歌》所说:“中国丝绸,你珍宝般的光彩,美化了我们生活”。
锦绣还与生活风俗结合,构成了一道道美丽精彩的民俗审美文化景观。譬如端午节有绣香包和送香包(南方人叫荷包)的风俗。制作的过程是:用丝绸包裹香草(如茱萸草,民间传说有驱邪功能)做成各种形状的小包,再在小包上绣各种图案,然后用彩绳作为香包的佩带。小孩将香包带在脖项,大人则是佩带在衣服上。送香包给小孩是保其平安,送给男孩或者女孩是传达爱情,送给老人是保其健康。在全国各地至今还流传着一些《绣荷包》民歌,其中大部分属于情歌。福建的《十绣荷包》则介绍了“绣荷包”的内容,诸如“狮子龙摆尾”、“鲤鱼跳龙门”和“鸳鸯戏水”等花纹图案,也寄托着人类对于幸福生活的期盼和美好的愿望。正如著名学者张道一所说,“她几乎要把中国的人文都绣到荷包中去了”。此外,还有婚俗中以丝绸锦绣制作喜服和鸳鸯被(合欢被)等,也很普遍。
在当代政治、外交、体育和科技等活动中,丝绸锦绣作为中华审美元素被广泛地使用着。譬如在政治方面:北京人民大会堂就悬挂着四大名绣精品,即江苏厅有苏绣《江南三月春意浓》、四川厅有蜀绣《芙蓉鲤鱼图》、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厅有粤绣《夏日海风》和金色大厅有湘绣《屏开花艳舞东风》。后者有五只孔雀,似与牡丹媲美,象征着祖国蒸蒸日上,繁花似锦。金色大厅20根红漆石柱上雕饰着金色祥云图案,犹如包裹着红地祥云锦绣一般,显得华丽富贵,典雅祥和;在外交方面:2014年北京APEC峰会上,男领导人服装采用提花万字纹宋锦面料,女领导人服装采用双宫缎面料,皆装饰着海水江崖纹,象征着我国政府的海洋发展的策略,也寄寓着我国愿与各经济体“山水相依,守望相护”的良好意愿,从而展示了中国人的新形象;在体育方面: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从运动员服装、火炬和获奖证书上,都能看到丝绸锦绣的祥云图案;在科技方面:2005年10月,以古蜀国标识“太阳神鸟金箔”图案为范本的蜀绣,搭载“神舟六号”飞船到太空中遨游。
总之,西方人认为“美”在艺术之中。因为真实的生活里充满了功利的欲望,是无美可谈的。但是,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则认为,“美”就在人的生活里,审美是一种高级生活方式。锦绣对于人类生活的美化,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文学艺术是中华传统审美文化的主要内容。锦绣与中华传统审美文化的关系,不仅表现在日常生活层面,而且也表现在文学艺术层面。正如我们难以将锦绣的实用与审美分开一样,我们也很难将文学艺术的实用与审美分开。对于中国人来说,丝绸锦绣与文学艺术都很重要,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既有实用的丝绸锦绣,也有实用的文学艺术;又有审美的丝绸锦绣,也有审美的文学艺术。因此,丝绸锦绣与文学艺术的关系是:
首先,丝绸生产、产品和生产者成为文学艺术表现的题材。道理很简单,因为丝绸生产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文学艺术反映社会生活时就必然会反映丝绸生产。所以,自古以来的文学艺术反映丝绸生产的作品较多。譬如诗,有《诗经·七月》、汉乐府的《陌上桑》、杜甫的《白丝行》和王建的《织锦曲》等;赋,有荀子的《蚕赋》、王逸的《机妇赋》和张率的《绣赋》等;古典小说《红楼梦》、《镜花缘》等对于丝绸锦绣有很多精彩的描写,当代小说有凌叔华的《绣枕》、阿蛮的《纪年绣》和日本作家宫本辉的《锦绣》等;音乐,除了前面谈到的各地民歌《绣荷包》之外,还有大家熟知的《绣金匾》和《蜀绣》等;电视剧有《锦绣缘》;绘画有唐代张萱的《倦绣图》和宋元时期流行的吴本《蚕织图》等,都是比较优秀的作品。再如宋代无名氏的《九张机》:“鸳鸯织就又迟疑,只恐被人轻裁剪,分飞两处,一场离恨,何时再相随。”作者将绣女复杂、细腻和微妙的心态刻画得惟妙惟肖。
其次,文学艺术作品中的人物、故事等也成为锦绣创作的题材。譬如古代叙事文学中的“嫦娥奔月”“西施浣纱”“贵妃醉酒”和“金陵十二钗”等,都是锦绣常见的题材。还有一些名人诗词、绘画和书法作品,也成为锦绣表现的对象,当然也有刺绣者创作的作品。据《晋书·窦滔妻苏氏传》记载:晋代秦州刺史窦滔被流放之后,移情别恋。其妻苏蕙思夫心切,便创作了回文诗,并刺绣在美锦上寄给丈夫。窦滔看后深受感动,与妻重归于好。这就是著名的“织锦诗”,或者叫“璇玑图”,计841字,婉转循环皆可读,共得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诗7958首。她不仅创造了一种诗体,而且成就了一段佳话。唐朝女皇武则天被其事感动,为《璇玑图》撰写了序文。明人梁桥的《冰川诗式》卷二对此事有记载。清人李汝珍的长篇小说《镜花缘》第四十一回描写了这一个故事。至于以缂丝的技法摹织名人字画始于宋代,成熟于明代。明代上海露香园顾绣是其代表。譬如明代顾绣代表人物韩希孟的《洗马图》就是一幅优秀之作。这幅绣品作于崇祯七年(1634),是在白色素地上刺绣,柳丝婀娜,骏马嘶鸣,马夫神态,都栩栩如生地反映出来了。绣者熟悉画理,所以将白马身上的花纹表现得如同绘画一般。画面素雅,显出一些高贵的气息。
苏绣和湘绣也以摹织名人字画见长。当代苏绣流派众多,佳作如云,几乎占了刺绣艺术的半壁江山。扬州苏绣大师陆树娴率领弟子,历时五年,以张大千晚年绝笔之作《庐山图》为范本,创作了大型水墨写意绣《庐山图》,绣画结合,大气磅礴,令人叹服。南通沈绣大师庄锦云和褚有莲合绣的《贵妃醉酒》,也值得欣赏。该作绣于1964年,以京剧大师梅兰芳扮演的《贵妃醉酒》剧照为范本,色彩丰富,针法多变,将人物醉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具备极高的审美价值。蜀绣《飞天》借鉴“嫦娥奔月”的构图,十分巧妙地以古蜀国标识“太阳神鸟金箔”取代了月亮,即以日代月,从而凸显了蜀绣的历史蕴含和艺术特色。总之,在当代锦绣中,徐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李苦禅的鹰、张大千的虎、郑板桥的竹、李方膺的梅和石涛的山水等,都是常用的题材。
再次,从古代词牌曲调里也会透露出丝绸锦绣对于文学的影响。古代青年男女聚少离多,绣女织妇经常独守空房,因而便出现了大量表现离愁别怨的歌曲,譬如宋代无名氏的《九张机》等。由于这些歌曲广为流传,后来就演变成词牌曲调了。如元代时《红绣鞋》歌曲很流行,后来被文人不断仿作,就成了一个曲调。
以上这些词牌曲调中都积淀着丝绸锦绣的审美元素,或是绣品,如绣鞋、绣衾、绣球;或是织锦,如锦标、锦帐、锦围;或是丝绸,如锦、绮、罗;或是工具,如绣针、剪子、捣子;或是花纹图案,如牡丹、彩鸾、福寿、一丛花、一剪梅、十样花、鹊踏枝、蝶恋花、彩凤飞等;或是丝绸生产,如采桑、采绿、捣练等。这些都是丝绸锦绣积淀在文学中的审美元素,不仅保留着历史信息,也是研究丝绸锦绣与文学关系的活文物。
锦绣是中华传统审美文化的花朵。在这些锦绣花朵上不仅凝聚着其生产主体中华女性的审美智慧,凝聚着其生产协作者中华男性的审美智慧,也凝聚着其观赏者的审美情趣,甚至凝聚着全社会的审美意识。因此,在这些锦绣花朵上积淀着深厚的中华传统审美文化意蕴,也积淀着丰富的中华传统审美文化信息。这些意蕴和信息最后都会表现到语言中来,从而绽放出一朵朵美丽的语言之花,形成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审美文化话语。
首先,丝绸锦绣渗透到日常生活之后,在中华传统社会审美文化层面形成了一些审美话语。在汉代以前,丝绸锦绣只是帝王贵族的生活奢侈品,如《盐铁论》所说“夫罗纨文绣者,人君后妃之服也”,一般平民百姓是不可以使用的。宋元以后,丝绸锦绣在平民生活中也得到了使用。因此,在人们观念中,丝绸锦绣既是美丽之物,也是珍贵之物,因而就进入了社会语言系统,形成了一系列社会审美话语。譬如广西壮族流行着一首《壮锦歌》云:“郎锦鱼鳞纹,侬锦鸭头翠。侬锦作郎茵,郎锦裁侬被。茵被自两端,终身不相离。”在这首歌里,锦、花纹、茵、被等锦绣话语,便成为传递爱情的情歌话语,显得含蓄缠绵,别有一番情调。
其次,由于丝绸锦绣与文学艺术的密切关系,使丝绸锦绣对于文学艺术创作、欣赏和批评活动进行了深度渗透,因而也就进入到了文学艺术语言系统,形成了一系列文艺审美话语。
此外,还有一些与丝绸锦绣有关的其他审美话语,诸如典故成语,有“锦书”、“衣锦还乡”、“衣锦夜行”、“锦上添花”、“花拳绣腿”、“锦绣年华”、“锦绣前程”、“锦绣中华”等。还形成了一些修辞方法,如“列锦”、“铺绣”等。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几千年来,由于丝绸锦绣对于中华传统审美文化的深度介入,形成了一个“锦绣”审美范式。所谓“锦绣”审美范式,就是以锦绣为审美标尺,来观照、衡量、命名和评价其他事物的美。这种审美观念认为,锦绣是“美物之首”,是美的典型,也是美的标准。甚至“锦绣”就是“美”,“美”就是“锦绣”。在中华传统审美文化的词典里,“锦绣”是“美”的同义词。如上所述,“锦绣”审美范式在审美话语层面,形成了“锦×”范式、“绣×”范式、“绮×”范式和“锦绣×”范式。这些审美话语范式,是丝绸锦绣审美文化的深层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