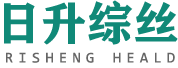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认定中的几个问题
摘要:《刑法》第114条与第115条第1款之间,存在未遂犯与既遂犯的普通结果犯和基本犯与结果加重犯的双重关系;行为人认识到公共危险并对危险结果持希望或放任态度便具有危险故意,进而发生具有认识可能性的实害结果,就成立危害公共安全罪。危险驾驶罪是故意的抽象危险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故意的具体危险犯,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三者区分重点是驾驶行为是否已对公共安全形成具体、紧迫、现实的危险。司法实践中,有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罪数认定十分混乱,存在滥用牵连犯理论、滥用连续犯理论、未准确认定行为数量等问题;行为人实施数个行为,符合数个犯罪构成要件,或者数次符合一个犯罪构成要件的,原则上应数罪并罚。

《刑法》第114条和115条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未规定具体行为结构与方式,而以“其他危险方法”进行的特殊罪状描述,其开放性使得司法实践中与危害公共安全相涉又无法与他罪构成要件相符的犯罪行为,大量统归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进行“口袋化”处理;同时其模糊性使得具体案件适用该罪名定罪时存在认定混乱的情形。比如,《刑法》第114条和115条第1款将危险和实害分别予以规定,这种特殊立法方式是立法者有意将公共危险犯与仅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区别对待,以加强对公共安全的保护,但现实中怎么样来判断危险故意和确定罪过形式存在争论;此外,在涉及公共安全的交通肇事罪、危险驾驶罪场合,常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难以界分,而有滥用该罪之嫌。对该罪的扩张适用趋势以及构成要件的模糊性问题,亟需进行限制性和精确性解释,以与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相洽,进一步指导司法实践。
主要有四种代表性观点:一是“基本犯与结果加重犯关系说”(简称“结果加重犯说”)认为,“第114条和第115条唯一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导致非常严重后果’,尚未‘造成难以处理的后果’的是危险犯,已经‘导致非常严重后果’的是其结果加重犯。尚未‘造成难以处理的后果’并不等于就是未造成任何后果,更不等于就是犯罪未遂。”[1]二是“未遂犯与既遂犯关系说”(简称“结果犯说”)认为,“刑法第114条所规定的危险犯和刑法第115条第1款所规定的实害犯之间,属于未遂犯和既遂犯之间的关系。”[2]三是“基本犯与情节加重犯关系说”(简称“情节加重犯说”)认为,“我国《刑法》第114条和第115条是基本犯和情节加重犯的关系……《刑法》第115条第1款和第114条的区别在于:由各种主客观因素影响导致的行为对同种法益在客观上的侵害程度不同。”[3]四是“结果犯与结果加重犯双重关系说”认为,当行为人对造成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伤亡实害结果具有认识并且持希望或者放任态度时,第115条第1款属于普通的结果犯,而第114条便是对第115条第1款的未遂犯的特别规定,可谓对未遂犯的既遂犯化的规定;当行为人只是对具体的公共危险具有故意,对发生的伤亡实害结果仅具有过失(并不希望或者放任实害结果发生)时,属于典型的结果加重犯,即两条之间是基本犯与结果加重犯的关系。[4]
笔者认为,上述争论的实质在于三点:一是形成了危险状态后是否还有犯罪中止成立的余地,若有,应如何具体适用刑法条文?二是仅具有所谓具体危险的故意,而无实害的故意的,是成立第115条第1款还是第2款?三是如何与将危险和实害规定于一个条文中的相关条文的理解相协调?
关于第一点,前面已有详尽论述,此处不赘。关于后两点,的确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认为只有对死伤结果具有希望或者放任态度的,才能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学者,通常反对将实施追逐竞驶、醉酒驾驶等危险驾驶而导致他人死伤结果的行为,评价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所持的理由是,由于危险驾驶者本人身处其中,一般不会放任包括自己在内的死伤结果的发生,因而仅成立交通肇事罪。
笔者认为,无论是将危险犯单独规定,如第114条、第116条、第117条、第118条,还是将危险犯与实害结果规定于同一条款中,如第123条、第124条、第141条、第143条、第144条、第145条、第330条、第332条、第334条第1款、第337条、第338条,并无本质的不同。也就是说,“这种将同一犯罪的不同形态在不同的条文中加以规定的做法,并不表示它是两种不同既遂形态的规定,而只是一种立法技术上的选择而已。”[5]即便如此,这种将危险犯单独设置法定刑的立法模式,毕竟不同于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等仅就实害结果配置法定刑的罪名立法模式。可以说,这是立法者有意将公共危险犯与仅侵害了个人法益的犯罪区别对待。既如此,在公共危险犯中,除实害故意外,应还存在所谓危险故意,即,刑法除规制实害结果外,还制裁所谓危险结果。因而,危险犯也可谓一种基本犯。质言之,为了加强对公共安全的保护,立法者特意将造成公共危险状态规定为一种基本犯,认为出于危险故意(基本犯故意)而发生了实害结果的,即便行为人主观上对实害结果可能仅具有过失,也能成立结果加重犯。
综上,笔者认为,为了加强对公共安全的保护,有必要承认危险故意与危险结果,肯定造成了危险状态即成立基本犯,出于危险故意(即认识到了公共危险并对危险结果持希望或者放任态度),进而发生了实害结果,即便行为人对实害结果并不持希望或放任的态度,但只要具有认识的可能性,就不妨碍故意的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成立。例如,只要危险驾驶行为人对(抽象或者具体的)公共危险存在认识,并对之至少持放任态度,如果实际造成了“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实害结果,就不妨碍第115条第1款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成立。也就是说,笔者赞成第114条与第115条第1款之间,存在未遂犯与既遂犯的普通的结果犯,和基本犯与结果加重犯的双重关系。
成立公共危险犯,既包括对实害结果具有故意的情形(结果犯),也包括不具有实害故意而仅具有危险故意的情形(结果加重犯),问题在于,如何判断危险故意和确定罪过形式?下面以危险驾驶案及私设电网案为例进行探讨。

在《醉驾意见》出台以前,对于醉酒驾驶致多人死伤的案件,一般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刑。即便出台了该意见,实务中控辩双方关于行为人的罪过形式是故意还是过失,案件是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还是交通肇事罪,争论仍然十分激烈,而法院的说理也基本上局限于《醉驾意见》中的相关表述,难以让人信服。
例如,(1)被告人吴某无证、醉酒(血液中的乙醇含量为147mg/100ml)驾驶轿车,碰撞到前方骑电动自行车的被害人邾某甲(最终死亡)后继续行驶,又碰撞到前方同向行驶的胡某驾驶的轿车。事发后,被告人吴某逃离现场。控方以交通肇事罪起诉。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吴某未取得驾驶资格证,醉酒驾驶机动车辆,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驾车逃逸,冲撞前方正常行驶车辆,发生追尾事故,仍继续驾车行驶,导致本人驾驶的车辆驶出路外滑入下坡,被迫停车,造成一人死亡、车辆严重损坏。被告人无视国家交通安全法规和公共安全,无证醉酒驾车,在交通事故发生后,没有主动采取措施,避免事故继续发生,而是驾车逃逸,连续发生多起交通事故,并造成一人死亡、公私财产受损的严重后果,证明被告人主观上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放任态度,严重危害了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财产安全,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于一审判决,检察院抗诉认为,吴某第一次发生的事故造成人员死亡应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面驾车逃离现场,虽发生事故,不宜认定为多起事故,没有造成重大伤亡,其行为符合交通肇事罪(逃逸)的构成要件。二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明确指出:…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造成重大伤亡,说明行为人主观上对持续发生的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对此类醉酒驾车造成重大伤亡的,应依法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本案中,上诉人吴某虽然无证醉酒驾驶机动车辆,碰撞致被害人邾某甲经抢救无效死亡,但其在逃逸途中与前方车辆发生追尾时,两次事故地点只相隔十几米远,时间相隔很短,事发当天又是阴天,水泥路面潮湿,事发路段有一弯道,被追尾的轿车当时也是因为看到前方路面有起伏踩刹减速,导致本案中的第二次事故的发生,导致轿车受损。因此抗诉机关认为原判适用法律错误,应认定为交通肇事罪的抗诉意见,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6]
笔者认为,由于根据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只有行为人在饮酒时就具有酒后驾驶的故意,才能认定为故意犯罪;本案中,如果不能查明行为人具有酒后驾驶的故意,则只能认定为交通肇事罪甚至无罪;如果能够查明行为人饮酒时就具有酒后驾驶的故意,则可能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醉驾意见》根据严重后果反推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故意,犯了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和本末倒置的错误;第一次肇事后进行连续冲撞,只是判断行为人主观罪过的一种资料,行为是成立(故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还是(过失)交通肇事罪,还是只能根据行为人饮酒时是否具有酒后驾驶的故意,实际驾车肇事时是否具有辨认或控制能力,来进行具体判断;司法实践中根据《醉驾意见》将醉驾连续冲撞致多人死伤的案件,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最重判处无期徒刑,说到底是因为,我国交通肇事罪法定刑偏低(交通肇事罪中“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几乎虚置),不能满足民众严惩醉驾的诉求,加之理论与实务将刑法第18条第4款“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错误地理解为法律拟制规定所致。
(2)2011年7月1日下午14时许,因土地权属纠纷,三十余名村民进入被告人戴某某承包的农场,将农场内种植的百余株罗汉松、玉兰树拔、砍、挖掉。当日15时30分许,戴某某得知后遂驾车赶回。当车行至湘潭市北二环线右拐驶进农场后,被告人戴某某虽踩刹制动,车速仍达57-59kmh,当场将村民刘某某(最终死亡)、李某某(轻微伤))、石某某(轻微伤)、许某某(轻微伤)、张某某(轻微伤)、杨某某(轻微伤)撞倒。戴某某下车后立即拨打110报警。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戴某某明知其高速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会发生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安全的严重后果,而放任该后果的发生,致一人死亡、五人轻微伤,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告人戴某某上诉认为,从认识因素看,上诉人事先并不知道村民聚集在进入农场的水泥路上,客观上没有预见到自己开的车进入农场后会撞到村民,而且根据本案《司法鉴定书》,上诉人进入种猪场后采取了应有的制动措施,由于进入农场时车速偏高,且上诉人不知水泥路上的站立人员及其与汽车的距离,完全超出了其所能预见的范围,对所造成的危害结果不能称其为明知;从意志因素来说,上诉人在右拐弯转入农场前尚未看到水泥路上的村民时,有打转向灯、鸣笛、采取中等制动的举动,在拐入农场看到村民时立即采取了紧急制动措施,于瞬间在后保险杆距离传达室1米左右的位置停车、熄火,上诉人采取了应有的和尽其所能的避免结果发生的措施,这些举动使得上诉人内心对于危害结果的发生,不能称其为放任;从事后表现看,事发后上诉人立即停车,用自己的手机先后8次拨打110报警电话,等待急救车和民警的到来,说明其并不希望死伤结果的发生。二审法院认为,证据表明上诉人戴某某案发前知道村民多人聚集在农场里,客观上应当预见自己高速驾车进入农场后可能会撞到村民,且现有的证据能证明上诉人戴某某进农场前车速较快,且未采取最大制动,表明其主观方面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不是疏忽大意没有预见,而是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本案事发地段在种猪场内,不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规定的道路范围内,上诉人戴某某有尽到安全注意和合理避让义务,其驾车撞到村民的行为不属于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调整范畴,发生事故致人死、伤的行为也不符合交通肇事罪的客观要件,其行为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客观要件。[7]
笔者认为,上述判决的说理十分混乱,应认定行为人主观上系过失,成立过失致人死亡罪。戴某某虽然事先知道有村民聚集在其承包的农场内进行破坏活动,但并不知道聚集的具置,也难以预见到村民就聚集在进入农场的位置,而且在看到村民前右转弯时有打转向灯、鸣笛、采取中等制动的举动,说明戴某某已经尽到了客观注意义务。而且从事发后的表现来看,也难以得出行为人希望或者放任他人死伤结果,即接受他人死伤结果的结论。虽然本案能以非发生在公共交通领域为由否认交通肇事罪的成立,但只要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并不希望或放任具体危险及村民死伤结果的发生,就只能论以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或者过失致人死亡罪的结论。从本案发生的周围环境来看,难以得出行为危害公共安全的结论,因而本案只可能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处罚。之所以成立过失致人死亡罪,是因为行为人明知有村民聚集在农场,其在驾车进入农场时应当减速,在右转弯时应采取充分制动措施以避免事故的发生,但其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结果的发生,以致最终酿成事故。
(3)“吴某、丁某追逐竞驶案”:驾驶中巴车的被告人吴某与丁某为争抢乘客,相互追赶、互不相让,不顾车上乘客安全并排高速行驶。两车行驶至沐阳收费站时,仍然互不相让,均不顾车上乘客及收费站工作人员等20余人生命安全,高速同时冲入仅允许一辆车通过的收费车道,被告人吴某驾驶的中巴车撞上收费岗亭,致使该岗亭和自己驾驶的中巴车报废,并致中巴车上乘客南某骨盆及胸部多处损伤、乘客刘某左上肢及脊柱损伤、乘客胡某面部及肢体多处损伤、乘客施某全身多处损伤,均构成轻伤。控方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起诉,被告人吴某辩称其主观上没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不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应以交通肇事罪论处。法院认为,被告人驾驶公共交通工具时,不顾公共安全,在公路上高速行驶,互相追逐,致多人轻伤,并致公私财产遭受损失,其行为均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告人吴某主观上受车主王某的唆使,明知车内有大量乘客仍高速行驶,并与被告人丁某驾车互相追赶,在进入收费站之前,明知仅允许一辆车通过,仍然与丁某的车并排行驶,同时高速冲入收费站, 其行为已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及交通安全造成威胁;被告人吴某对其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放任发生,属间接故意。[8]
笔者认为,被告人明知车上载有大量乘客还高速追逐竞驶,甚至同时高速冲入仅允许一辆车通过的收费车道,表明被告人明知具体危险的存在还执意实施,具有危险故意,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因而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司法实践中,对于私设电网案罪过形式的认定十分混乱。例如,有的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1)被告人杨某甲为猎捕野生动物,擅自在山林中架设电网,长度约1500米,为防止伤人,被告人杨某甲每天18时许打开电源,次日凌晨6时许关闭。某日凌晨3时许,被告人杨某甲私设的电网电死一只省级二级保护动物黄麂,产生的火花导致森林失火。法院认为,被告人杨某甲未经有关部门批准擅自在山林中架设电网,对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及公私财产造成安全隐患,危害公共安全,并造成电死一只省级二级保护动物和导致森林失火的危害后果,其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9](2)被告人吴某为防止其瓜田的西瓜被盗和瓜藤被破坏,在瓜棚东面1米处设置了用竹子拦成的150米长篱笆,在竹篱笆内侧拦了尼龙网,并在瓜棚东端私自架设用上中下三根串联的细钢丝横拉成的电网,并在夜间保持通电状态。某日晚8时许,邬某与赵某酒后至吴某瓜田偷瓜时,邬某遭电击倒地。吴某发现后即对邬某施救送医,并拨打110报警,后邬某经抢救无效死亡。法院认为,被告人吴某的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10](3)被告人王某以野猪破坏庄稼为由,在未经有关部门批准、未设任何警示和升降压装置的情况下,私自在其家用照明电线上搭设电线至其责任田,并在田埂周围用细铁丝在竹片上接上电线,私自搭设电网,每天晚上拉闸通电,天亮前断电。某日晚9时许,十一岁的被害人王某在放水时不慎触电死亡。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为防止野猪侵害庄稼,违法私自在自家责任田架设电网,应当知道其行为会危及不特定人的生命安全,却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以致发生他人触电死亡的严重后果,被告人的主观心态属间接故意,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11](4)被告人李某、张某为捕捉野兔,在村中路边麦田私设电网。晚上9时左右将电网通电,次日凌晨3时许,顺着小路找猪的被害人李某触电而死。二被告人发现后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并报警。法院认为,被告人明知在村民通行的路上等公共场所私设电网危害公共安全而仍然为之,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12]
有的认定为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5)被告人何某为防盗,晚上11时许将电线接到自己的金属卷闸门上,致该门通电。次日上午7时许,小学生林某上学途径此处被电击致死。法院认为,被告人何某无视国家法律,为个人利益而在公共场所非法以使金属卷闸门带电的方法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安全,并对该行为的危害结果采取轻信能够避免的心理态度,致使林某触电而死,已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13](6)被告人催某为猎捕野生动物,在国营林场防火通道上安装高压电网,后将骑摩托车进山捡核桃途经此道的被害人刘某电击致死。法院认为,被告人崔某作为国营林场护林人员,在野外以安装高压电网的危险方法猎捕野生动物,本对可能发生危害公共安全的严重后果应当预见,但因疏忽大意和缺乏相关法律、科学知识而没有预见,以致造成不特定的他人触电休克死亡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14](7)被告人许某为阻止他人盗瓜,于2008年6月左右,在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红星村1604号北侧由其承包的西瓜地内私自架设了电网。同年7月7日晚至次日凌晨,许某将电网接通220V交流电,致被害人余某被电击身亡。后公安机关经现场勘查,发现漏电保护设备。法院认为,许某从一般人的认知处罚,认为只要安装了漏电保护设备,就不会致人死亡,没有对漏电保护设备是否有效进行检验,以致漏电保护设备实际因客观原因未能发挥保护作用。这表明许某过于轻信能以安装的漏电保护设备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主观上持过失的心理态度,而无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故意。其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15](8)被告人范某为狩猎和保护庄稼,在自家房后的耕地旁、山林内架设“电猫”,“电猫”电源设在自己家中,电线从其家中引出,横穿范某屋后与范某承包地之间的一条乡间小路。为防止“电猫”伤人,范某用一根较长的竹竿将横在这条乡间小路上的这一段“电猫”线撑起,平时不会影响村民通过,范某某采取夜晚给“电猫”通电,白天关闭“电猫”电源,并将其设置“电猫”的情况告诉周围邻居,让邻居晚上不要到设“电猫”的区域去。后将上山打猎经过此地的张某电死。法院认为,被告人范某为狩猎和保护庄稼,在自家耕地外围的荒地、林地内私设“电猫”,虽地处偏僻,但并不封闭,不能排除不特定人员的进入,故其私设“电猫”的行为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安全。被告人范某明知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私设“电猫”,应当预见该行为可能发生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生命、健康安全的危害结果,却以采取私下通知附近村民注意安全和夜晚通电等预防措施,而轻信可以避免,最终造成了被害人张某触电身亡,其行为已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16](9)2014年8月6日,被害人方某某邀约被告人欧某某用拉电网的方式捕猎野猪。次日16时许,欧某某与方某某在云阳县外朗乡五峰村方某某家附近用细铁丝架设电网。欧某某给电网设置了拉线开关,约定由方某某负责每天晚上通电,早晨断电,但由于欧某某操作失误,电网开关并不能线日上午,方某某不慎触碰到电网时被电击身亡。法院认为,被告人欧某某在未采取有效措施的前提下私设电网,已经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的危害结果,但轻信能够避免,导致被害人方某某死亡,其行为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17]
笔者认为,行为人通常都是选择在村边、山林等偏僻之处,而非在人流量大的繁华闹市区,而且行为人往往采取夜间通电白天关闭、设置保护措施或警告周围人等方式防止伤及无辜,事发后通常都能第一时间施救报警,事实上都仅导致个别人触电致死伤而案发,而鲜见一次就致使多人触电身亡的案例,这说明,实践中发生的私设电网案并不危及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安全,结果不具有扩展性、蔓延性、不可控制性,行为不具有与刑法第114条、第115条放火等罪的危险相当性,行为人对实际发生的严重后果通常是希望其不发生,即不接受结果的发生,而非希望或者放任其发生。因此,对于私设电网案,除极端例外情形外,如设在人员频繁出入的地方、白天通电、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均宜论以过失致人死亡罪或者过失致人重伤罪。
此外,“公共安全”中的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显然不包括本人和同伙的安全。例如,交通肇事罪中“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显然不应将肇事者本人的车辆损失计算在内。案例(9)中,是被害人方某某主动邀约欧某某私拉电网,风险显然应自我承担。因操作不当致本人死亡,应属“咎由自取”,不应让他人(包括同伙)对其死亡结果负责。也就是说,危害公共安全罪并不同于聚众斗殴罪之类的扰乱公共秩序的犯罪,行为人不必对同伙的死伤承担刑事责任。
关于三罪所属犯罪类型及三罪之间的关系,理论上的基本共识是,危险驾驶罪是抽象危险犯,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的实害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属于具体危险犯;分歧主要在于,危险驾驶罪是故意的抽象危险犯还是过失的抽象危险犯,以及交通肇事罪是否属于危险驾驶罪的结果加重犯。[18]
刑法理论公认,我国刑法仅处罚过失的实害犯,而不处罚过失的危险犯。[19]既然连过失的具体危险犯都不具有刑事可罚性,怎么可能单单肯定过失的抽象危险犯的可罚性呢?所以,主张危险驾驶罪的主观方面可以是过失的立场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交通运输是现代社会中被允许的危险行为。虽然危险驾驶行为除追逐竞驶、醉酒驾驶外,还有无证、超速、超载、疲劳、逆向等危险驾驶行为,但立法者认为追逐竞驶与醉酒驾驶具有类型性的抽象危险,故而特意将故意追逐竞驶与醉酒驾驶造成抽象危险的情形予以犯罪化。而只要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对事故结果至少具有过失的,就成立交通肇事罪,因而成立交通肇事罪的违规行为比危险驾驶罪所规制的情形要广泛得多。既然成立交通肇事罪并不以行为成立危险驾驶罪为前提,讨论交通肇事罪与危险驾驶罪是否基本犯与结果加重犯的关系并无实际意义。正如讨论作为抽象危险犯的非法制造爆炸物罪与爆炸罪之间的关系并无实益一样。有实质意义的是,危险驾驶同时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是成立交通肇事罪一罪,还是成立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数罪?从理论上讲,只要危险驾驶行为与交通肇事行为没有重叠,可以在规范性意义上理解为两个行为,例如醉酒驾驶十公里后肇事的,就可能成立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数罪进而数罪并罚。
此外,理论上一般认为,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交通肇事罪之间,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根据法条竞合原理,应以特别法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20]实务中也有判例肯定这一点,认为“《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的‘交通肇事罪’是一个普通条款和特殊条款的关系,属于法条的竞合,当出现交通肇事情形时就不再适用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条款”[21]。不过,司法实践中还是存在不少本应认定为交通肇事罪的案件,定性为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例如,行为人醉酒后坐在副驾驶位置上发现车辆倒退,慌乱中踩到油门导致车辆失控;[22]因车辆爆胎而将车辆停在应急车道,未放置警告标志,导致与后面驶来的车辆相撞;[23]为挣断扣押汽车的钢丝绳,在公共场所强行高速驾驶机动车,导致车辆失控冲向市场巷道。[24]值得一提的是,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基本刑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重于交通肇事罪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基本刑,导致以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实际判处的刑罚可能重于交通肇事罪。笔者认为,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基本刑是针对一般的过失危险行为而言的,而交通肇事罪因为存在交通运输是被允许的危险行为这一客观情况,故而基本刑低于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换言之,考虑到交通运输系被允许的危险行为,即使论以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首选的法定刑也应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并非是所谓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特别关系法条竞合原理决定的,而是体系解释得出的结论。
关于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界分,从理论上讲,二者的区别在于危险的程度不同,前者是抽象危险,后者是具体危险;是抽象危险还是具体危险,取决于个案中的具体判断,但司法实践中的认定和说理较为混乱。
例如,(1)被告人钟某醉酒驾驶(血液中乙醇含量为345.45mg/100ml)轻型货车先后与张某忠、吴某驾驶的轿车、张某溪驾驶的二轮摩托车、沈某驾驶的客车、邱某、赖某及俞某驾驶的轿车相撞,并冲撞多家店铺和摊位。一审认定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告人上诉提出应以危险驾驶罪定罪量刑。二审法院回应指出,“上诉人钟某醉酒驾车撞车后,继续驾车行驶,连续冲撞多部车辆、多家店铺和摊位,造成多人的经济损失,主观上具有对不特定的人身、财产等危害结果的发生持放任态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间接故意,故上诉人及其辩护人的诉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25]
其实,主张成立危险驾驶罪的上诉意见,也并没有否认行为人主观上至少具有间接故意。所以,是成立危险驾驶罪还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而在于危险驾驶行为造成的是对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身体安全的抽象性危险,还是具体、现实、紧迫的危险。就本案而言,行为人醉酒后完全失去驾驶车辆的能力,以致车辆在道路上横冲直撞,若不考虑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单就客观状态而言,驾驶行为无疑已经形成了具体性危险,故符合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客观要件。总之,是成立危险驾驶罪还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断的关键在于行为的危险程度。
(2)被告人蔡某醉酒驾驶(血液中乙醇含量为201.3mg/100ml)轿车,在倒车时轿车左后部驶入路边绿化带,右后部撞到人行道的路灯杆,随后继续驾驶。民警接到群众报警后设卡拦截。蔡某为逃避检查,驾车加速越过三道岗哨,并将民警刘某顶撞在轿车前部引擎盖上行进约20余米,后猛打汽车方向盘将刘某甩落致肢体多处擦挫伤,之后相继撞上同向行驶的梁某驾驶的轿车和相向行驶的许某驾驶的轿车。控方以危险驾驶罪起诉。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蔡某明知醉酒驾车会危害公共安全,却无视法律,醉酒后驾车在公共道路上行驶,后为逃避检查,以驾车加速冲卡、撞人、撞车等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致一名交通警察受伤,两辆轿车先后被撞受损,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蔡某实施的上述行为,均是在一个犯罪故意支配下的行为,根据‘一行为一罪’的刑法理论,其行为仅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公诉机关指控的危险驾驶罪不能成立。”被告人蔡某以其行为应该构成危险驾驶罪为由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回应指出,“蔡某血液中乙醇含量201.3mg/100ml,远超80mg/100ml这一认定醉酒驾驶的标准。该节结合蔡某在倒车时便将‘轿车左后部驶入路边绿化带,右后部撞到人行道的路灯杆’分析,蔡某在案发时已无法正常控制驾驶的车辆。证人万某、卢某的证言与被害人许某、梁某、刘某的陈述能印证证实,本案案发时间系高考学生进入考场时间、案发地点系闹市区高考学生考场地点,即案发时间、地点的人车流量均较大;蔡某驾驶车辆速度较快,并非缓慢;在执勤民警刘某被动趴伏在车辆引擎盖上时,蔡某并不立即停车,反是将其甩下车辆,后又撞上许某、梁某驾驶的轿车。以上证据间能综合证实,蔡某在无法正常控制驾驶的车辆时,不顾‘民警被其甩落后可能被旁边或自身驾驶的车辆碾压’和‘碾撞其他行人与车辆’的危险,快速在人车流量较大的闹市区行驶,且业已发生执勤民警肢体多处擦挫伤及二辆轿车被撞的实际危害后果。因此,本案中蔡某的行为已侵害了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财产安全,且造成相关危害后果,故应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本案定性正确。”[26]
笔者认为,即便不考虑醉酒驾驶这一情节,仅从将车倒入绿化带、加速冲卡、拖拽被害人、连续冲撞多辆车,就不难得出蔡某的危险驾驶行为,已经对公共安全形成具体、现实、紧迫的危险,虽然成立作为抽象危险犯的危险驾驶罪,但也不能否认同时成立作为具体危险犯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且,若明知被害人刘某被顶在汽车引擎盖上还继续高速行进,甚至猛打方向盘将被害人甩落,则还符合了故意杀人罪(未遂)构成要件。所以,从理论上上讲,本案不能排除成立危险驾驶罪(醉酒驾驶)、故意杀人罪(拖拽被害人)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连续冲撞多辆车)三罪进而数罪并罚的可能性。
(3)被告人买某某感觉在与曹家父子殴斗中吃了亏,就驾驶面包车撞向曹家父子三人,三人及时躲开。曹某甲躲开后驾驶自家的面包车与买某某驾驶的面包车在省道308上追逐互撞,相互追逐大约几十米,导致两车不同程度损坏。被告人辩称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法院认为,“买某某因感觉与曹某乙父子打架过程中,自己吃亏,出于报复目的先行驾车撞曹某乙父子,后曹某甲也驾驶车辆与买某某互撞,二人驾车互撞的地点是在省道上,系公共场所,且事发时间为11时左右,其可能侵害的对象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结果事先均无法预测,也难以控制,其行为危害到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公私财产以及公共生活的安全,侵害的法益并非单纯的财物所有权,而是社会公共安全,损坏财产权仅是社会公共安全的内容之一,其行为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应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27]
笔者认为,本案应将买某某故意驾车撞向曹家父子的行为,认定为故意杀人罪未遂;之后相互撞车,应视为被害人承诺的行为,不成立故意毁坏财物罪;虽然二被告人是在省道上追逐互撞,但距离仅几十米,谈不上追逐竞驶,故不成立危险驾驶罪;案情并未交代,短短几十米的追逐互撞是否危及其他人车的安全而形成具体、紧迫、现实的危险,故也难以肯定作为具体危险犯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成立。
综上,区分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关键在于,危险驾驶行为是否已对公共安全形成具体、紧迫、现实的危险;只要行为的主要部分并不重合,则不能排除以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数罪并罚的可能性。[28]
关于二罪的区别,刑法理论通说认为,关键在于主观罪过,前者是故意犯罪,后者是过失犯罪。[29]司法实践中,凡是被告人辩称应成立交通肇事罪而非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案件,法院判决中几乎千篇一律地回应指出,行为人主观上至少出于间接故意,所以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非交通肇事罪。有判决书为证:(1)“判断被告人莫某的行为究竟是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还是交通肇事罪的核心是看其犯罪时的主观心理状态,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为故意犯罪,行为人对危害后果持积极追求或放任的心态;交通肇事罪为过失犯罪,行为人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危害后果,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危害后果,具体到本案就是判断被告人莫某醉酒肇事后逃逸时对危害后果是持放任态度还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被告人莫某醉酒驾车肇事之后,为逃离现场继续驾车冲撞,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造成重大人身伤亡以及财产损失,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30](2)“关于上诉人及辩护人提出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本院认为,杨某明知酒后驾车违法,醉酒驾车会危害公共安全,却无视法律,严重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在城市主干道上行驶,发生交通事故后,更应认识到继续驾驶车辆会危及公共安全,但继续驾车逃离现场,放任危害结果发生,又发生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一人受伤后再次逃逸。上诉人主观上对连续发生的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行为危害了公共安全,并导致非常严重后果,应当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31](3)“从本案事实及证据证明的情况看,被告人购置汽车以后,未经正规驾驶培训及考核获得驾驶资格证,无证驾驶车辆。被告人梅某某在明知国家规定的情况下,仍漠视社会公众和重大财产的安全,藐视法律、法规,无证驾车行驶,在超过醉酒标准3倍多的情况下,仍在车流量大、行人多的道路上驾驶未定期进行安全检查的机动车快速行驶,事实表明,梅某某对其行为可能造成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完全能够预见,虽不是积极追求这种结果发生,但属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其行为完全符合刑法关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规定,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32]
问题是,二罪的区别是否仅在于主观方面,或者说,除主观方面不同外,是否首先表现为客观方面的差异?撇开原因自由行为不谈,《醉驾意见》之所以将醉酒肇事后连续冲撞的案件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个重要的理由应该在于,肇事后慌不择路、横冲直撞的驾驶行为,已经对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身体安全形成具体性危险,而实际发生的连续冲撞事故,不过是判断行为已经形成具体性危险的一种资料而已。换言之,即便肇事后的逃逸行为因其他人、车躲让及时,而未实际发生碰撞,或者首次肇事就发生重大事故,只要根据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形,能够判断已经形成具体性危险,而且行为人对具体性危险存在认识并至少放任具体危险的发生,就可以肯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成立。正因为此,发生在北京附近的“陈家醉酒驾车案”中,陈家饮酒后超速驾驶撞向前方正停车等候交通信号灯的被害人驾驶的菲亚特小型轿车,致对方车毁人亡,被法院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33]同样,司法实践中,对于无证驾驶并连续冲撞致人死伤、[34]高速行驶致人死伤、[35]追逐竞驶致人死伤、[36]追赶、别、挤、逼停他人车辆致人死伤、[37]快速倒车、加速逆向行驶、“S”形路线]以及故意撞击他人车辆致死伤[39]等危险驾驶案件,之所以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也是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形,判断认为驾驶行为已经对公共安全形成了具体性危险,而且行为人对具体危险存在认识并至少持放任态度。否则,也只能论以交通肇事罪。
综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交通肇事罪的区别,虽然也表现为罪过形式的差异,但究其根本,还是在于驾驶行为所形成的危险程度的差异。质言之,只要驾驶行为本身已经对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生命、身体安全形成现实、紧迫、具体性危险,而且行为人对所形成的具体性危险存在认识并至少持放任态度,就符合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构成要件,否则,只能论以交通肇事罪。
根据罪数理论,行为人实施数个行为,符合数个犯罪构成要件,或者数次符合一个犯罪构成要件的,除非刑法已经将多人次规定为加重情节并规定加重法定刑,如妇女多人、拐卖妇女多人,或者可以通过数额或者数量的累计计算而适用加重法定刑,如多次盗窃、诈骗,即使不数罪并罚也能做到罪刑相适应,否则,原则上应当数罪并罚。[40]但司法实践中,有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罪数认定十分混乱。主要表现在:
例如,被告人管某酒后(血液中乙醇含量为130.8mg/100ml)得知其被曲出所民警追缴,遂驾驶载有液化气钢瓶的轿车到曲出所大门处,被值班民警拦截。被告人管某坐车车内打开液化气钢瓶阀门并将打火机拿在手中威胁在场民警,后经劝说才关上阀门,打开车门下车。法院认为,“被告人管某为泄私愤,酒后驾驶载有液化气钢瓶的机动车到公共场所,打开液化气钢瓶阀门,并拿打火机准备点火,使不特定人员生命和公共场所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告人管某醉酒后驾驶载有液化气钢瓶的轿车去曲出所的行为虽构成危险驾驶罪,但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系牵连性犯罪,而牵连性犯罪构成数罪的,应择一重罪处罚,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管某犯危险驾驶罪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以被告人管某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41]又如,司法实践中,对于“碰瓷”案,仅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罪进行评价,而不评价向对方勒索钱财的敲诈勒索行为。[42]很显然,也是认为“碰瓷”案中故意撞车这一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与向对方勒索钱财这一侵害他人财产权的行为之间,存在所谓牵连关系,根据牵连犯理论而从一重处罚。
对于刑法理论上的所谓牵连犯概念,目前国内有不少学者主张取消。[43]笔者也赞成取消,主张将原先作为牵连犯处理的问题,分别作为想象竞合犯、包括的一罪和数罪并罚处理。一则,我国刑法分则关于牵连犯的规定并不统一,有规定从一重处罚,有规定独立的法定刑,亦有规定实行数罪并罚。[44]二则,我国已经将国外所公认的典型牵连犯,如入户盗窃、入户抢劫专门做出规定。至于入户、入户杀人,并不具有类型性牵连关系。三则,牵连犯原本就侵害数个法益,符合数个犯罪构成要件。四则,牵连犯因为是科刑的一罪,会产生一事不再理效力。这也是我国台湾地区2005年修订刑法时删除牵连犯的主要原因之一。[45]日本在1974年改正刑法草案中删除牵连犯规定,也是出于这一考虑。[46]
上述管某案中,很显然,醉酒驾驶的危险驾驶行为与之后的以点燃液化气相威胁而危及公共安全的行为,虽然侵害法益同属于公共安全,但明显属于两个不同的行为,没有理由不以数罪进行并罚。正如非法购买爆炸物进而实施爆炸,没有理由不以非法买卖爆炸物罪与爆炸罪进行数罪并罚一样。否则,就会与非法购买后用之杀人,成立非法罪与故意杀人罪进而数罪并罚的处理不协调。
例如,自2004年4月以来,以李跃等人为首的犯罪团伙,在北京市主干道以及部分高速公路上多次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并以此向“事故”的另一方当事人索要钱财。其采用的作案手法主要是,由被告人李跃等人驾车在道路上寻找外省市进京的中、高档小轿车并尾随其后,当前车正常变更车道时,突然加速撞向前车侧后方,造成前车变更车道时未让所借车道内行驶的车辆先行的假象。“事故”发生后,其他被告人轮流冒充驾驶人,待到达事故现场的交通民警做出前车负全部责任的认定后,以此要挟甚至采用威胁的方法,向被害人索要钱财。31名被告人先后制造对方负全部责任的事故220余次,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51万余元。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李跃等人的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最终判处九年六个月有期徒刑。[47]
将上述多次实施“碰瓷”即故意撞车的行为,认定为一罪,显然与仅实施一次也被认定为该罪的处罚不协调。[48]而之所以将多次实施一种行为、多次符合同一犯罪构成要件的仅认定成立一罪,显然是将这种情形看做连续犯,并根据所谓连续犯理论从一重处罚。
其实,理论上所谓的连续犯概念,也应取消。对于数额犯、数量犯,数额、数量累计计算即可。除此之外,以前作为连续犯处理的,只要不能评价为某罪的加重情节(如妇女多人、拐卖妇女多人),一律作为同种数罪并罚。一则,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之所以废除原法律中规定的连续犯概念,以及德国1994年刑事庭决定放弃连续犯概念,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在规定了严格办案时限的今天,因受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约束,保留连续犯概念,无疑等于纵容犯罪。[49]二则,实践中不分所侵害的是否属于个人专属法益,在同种数罪不并罚的通说背景下,[50]滥用连续犯概念,难免罪刑失衡。三则,根据所侵害的是否属于个人专属法益,是否数额、数量犯,能否评价为某罪的加重情节,对原来作为连续犯处理的行为分别进行处理,就能够避免罪刑失衡以及因一事不再理效力所导致的对犯罪的打击不力。
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言,显然未将多次实施的规定为加重情节进而加重法定刑。该罪基本犯的法定刑仅为十年有期徒刑,如果将实施无限多次的情形(如上述“李跃碰瓷案”)与仅实施一次或者几次的情形,均以一罪论处,显然难以做到罪刑相适应。虽然通说仍在顽固坚持判决宣告前的同种数罪原则上不并罚,[51]但是,“‘一罪一刑’的罪刑关系、行为责任论、量刑情节的差异性等原理与事实,决定了对判决宣告以前的同种数罪,原则上应当实行并罚”[52]。因此,对于多次实施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原则上应当实行数罪并罚。否则,就与既放火又爆炸而以放火罪与爆炸罪数罪并罚的处理不相协调,也有悖罪刑相适应原则。
刑法第133条之一第2款规定,危险驾驶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问题在于,如何理解这里的“同时”?所谓同时,应当是指行为主要部分基本重合。换言之,如果行为主要部分并不重合,而是可以评价为数个行为,则不能适用上述从一重处罚的规定,不能排除数罪并罚的可能性。
例如,被告人吴某某在饮了半斤左右白酒后(经检测血液中乙醇浓度为116mg/100ml)驾驶越野车与潘某某一起离开。20时50分许,当车辆行驶至某路段时发现交警正在检查酒驾,为逃避检查,吴某某快速逆向倒车逃跑,交警打开警车车灯进行拦截,被吴某某撞上车门,车内协警岑某某被甩出车外、高某被撞伤。被告人吴某某仍未停车,继续逆向倒车后向北行驶。后撞到交通标志牌弃车逃离。法院认为,“上诉人吴某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同时吴某某在县城区路段醉酒驾车,为逃避酒驾检查和处罚,不顾公共安全快速倒车,在与一辆执法警车发生碰撞并造成人员受伤后,仍置公路行人和其他行驶的车辆安全于不顾,继续驾车高速逃离,足以说明其明知酒后驾车违法、醉酒驾车会危害公共安全,却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主观上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间接故意,虽然未造成难以处理的后果,但足以威胁到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及其他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其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根据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二款的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量刑,故一审法院对吴某某的行为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并无不当。”[53]
该案中,被告人醉酒驾车在遇到警察拦截前,无疑属于危险驾驶行为,这与其后的快速逆向倒车、碰撞警车、快速逃离的行为并不重合。也就是说,在遇到警察之前的危险驾驶行为,仅具有抽象性危险,成立危险驾驶罪;之后的行为由于已经对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身体安全形成具体性危险,因而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既然前后行为并不重合,没有理由不数罪并罚。正如,因疲劳驾驶发生致人死亡的交通事故后,而慌不择路地逃逸又连续冲撞多辆车的,没有理由不以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数罪并罚一样。
司法实践中也有正确认定了罪数的判例。例如,被告人宋某某驾驶轿车,在路口未确保安全,与骑人力三轮车闯红灯的被害人严某发生碰撞,造成严某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同时造成被告人宋某某所驾驶车辆的前挡风玻璃中部发生网状破碎。发生事故后,被告人宋某某在视线模糊的情况下驾车逃逸,又与骑自行车的沈某发生碰撞,但被告人宋某某仍未停车继续驾车前行,沈某亦被带离现场一段路程后被甩下。宋某某仍未停车继续逃逸,直至车辆再次发生撞击而熄火。法院认为,宋某某的行为同时构成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数罪并罚。[54] 笔者认为,该判决认定数罪进而数罪并罚是正确的。因为前后两个行为并不重合,根据“一罪一刑”原理,应当数罪并罚。
总之,对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相关行为,如果行为主要部分并不重合,可以分别评价为数个行为的,无论是数个行为分别符合不同犯罪的构成要件,还是数次符合一罪构成要件,为了对行为进行精确评价和做到罪刑相适应,原则上应当数罪并罚。
《刑法》第114条与第115条第1款之间,存在未遂犯与既遂犯的普通的结果犯,和基本犯与结果加重犯的双重关系。也即,成立公共危险犯,既包括对实害结果具有故意的情形(结果犯),也包括不具有实害故意而仅具有危险故意的情形(结果加重犯)。认识到公共危险并对危险结果持希望或者放任态度便具有危险故意,出于危险故意进而发生实害结果,即便行为人对实害结果并不持希望或放任的态度,但只要具有认识的可能性,就成立故意的危害公共安全罪。
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不同之处在于危险的程度不同,前者是抽象危险,后者是具体危险;是抽象危险还是具体危险,取决于危险驾驶行为是否已对公共安全形成具体、紧迫、现实的危险。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交通肇事罪的区别,前者是故意,后者是过失,且只要驾驶行为本身已经对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生命、身体安全形成现实、紧迫、具体性危险,而且行为人对所形成的具体性危险存在认识并至少持放任态度,就符合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构成要件。
司法实践中,有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罪数认定十分混乱,存在滥用牵连犯理论,滥用连续犯理论,未准确认定行为数量等问题。对原先牵连犯场合,侵害同属公共安全法益但明显属于两个不同行为的,应数罪并罚;对多次实施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原则上应当实行数罪并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相关行为,如果行为主要部分并不重合,可以分别评价为数个行为的,无论是数个行为分别符合不同犯罪的构成要件,还是数次符合一罪构成要件,原则上应当数罪并罚。